天台山之旅:体验“山中白云闲”的宁静


小艾 /摄
天台山有仙山之名,由来已久。东汉末年道教兴起,东吴年间,葛玄初至天台山,见山上云雾缥缈,山岚氤氲,霞光映照,一派仙家气象,不由得心生欢喜。后来他在桐柏山炼丹传道,仙山之名因此远扬。仙风浩荡,高道司马承祯觐见唐玄宗,唐玄宗即以葛玄之天台,称先生之来处。唐代道教鼎盛时期,一座方圆不过几公里的桐柏山,就有二十多座宫观跻身其中。葛玄眼中的天台山是“高高山上山,山中白云闲。”云与雾本质上都是一团团遇冷的水蒸汽凝结而成的小水滴,贴近地面的为雾,有一定高度的则为云,山中缭绕的成团水汽,云雾莫辨,或谓雾更妥。白居易写仙山“忽闻海上有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。”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,述及天台山时,言道:“云随羽客,在琼台双阙之间。”仙人降临,腾云驾雾。仙山自有洞窟幽奇,修真灵境,至于因何以缥缈?全凭云遮雾罩之功,若一览无遗,此中又有何异趣,怎么成为众妙之门。云雾缭绕成了仙山的标配。

天台山濒临东海,来自东海海面的大量水汽在山麓爬坡抬升,气温降低,凝结成雾。许多植物喜欢多雾潮湿的环境,茎叶饱受水滴滋润,颇得风调雨顺的气象,茶树就是其一。葛玄在华顶山麓开圃植茶,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茶祖,归云洞边有片次生茶树林,树龄在千年以上,相传是葛玄当年手植之物,可见天台山植茶之悠久。洞边有石,风化侵蚀,上题“葛仙茗圃”四字。天台山各地都产云雾茶,唯以圃中所产云雾茶为最,外形细紧,绿润披毫,香气浓郁持久,其味清洌回甘,汤色嫩绿明亮,有“佛天雨露 帝苑仙浆”之美称,是绿茶珍品。仙人羽衣飘飘,迎风抚琴,沏一壶云雾茶,仙家的岁月就在华顶山上缓缓展开了。

雾虽不能与降雨相比,带来丰沛的水量,但可以作为降水的一种补充形式。叶片上布满绒毛,可以吸附水汽,凝结成水滴,并输送给根部。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,连续几十年不见降雨,却并非生命禁区,细究之下,发现那里的植物就靠叶面吸收水汽,来维持生命,而羊驼之类食草动物则会在清晨的浓雾中舔食叶面上的水滴,而不至身体脱水。华顶山多雾,是植物生长的乐园,山上各种珍稀植物目不暇接,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云锦杜鹃。华顶山有一片天然杜鹃林,面积有三百亩之巨,多数树龄在二百年之上,上千年的亦不鲜见。五月的华顶山,云锦杜鹃竞相绽放,漫山遍野,如云似海,堪称华夏一绝。

公元1613年5月22日,云锦杜鹃像往常一样开满山岗,华顶山北麓迎来一名过客,在他眼里,“琪花玉树,玲珑弥望”当时他二十八岁,一介布衣,再过几十年,他才声名大噪,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霞客。清康熙年间张联元知台州,对云锦杜鹃颇为溢美,他写过一首《杜鹃花》诗曰:“翠岫从容出,名花次第逢。最怜红踯躅,高映碧芙蓉。琪树应同体,桃源许并秾。无人移上苑,空置白云封。”张联元将别名红踯躅的云锦杜鹃与仙界琪树、碧桃花相比,既赞叹它有旷世之美,又感慨它没有收入皇家花园之境遇,沦落山野,伴闲云长风,殊色无人赏识。张联元为官一方,对地方风物不免偏爱,他有所不知的是,云锦杜鹃通常只生长高海拔地区,阴冷湿润环境,虽然也有山下花苑移栽成功的范例,和生长华顶山上相比,已然没有了超脱凡尘之感。我有一次雨后登临华顶,山上薄雾弥漫,穿行石径上,雾中看花,花非花,雾非雾,绿叶浮在雾水上,曲折的虬枝游离于流淌的浓雾中,恰似一幅浓淡相宜的大写意水墨画卷,那么荒诞不经,惊艳了时光。疑惑此景不应人间有,莫非是身在梦中?

白云飘过,白墙黑瓦的人家如星辰般闪现在天台山上。山里人勤劳,在田间地头种些瓜果蔬菜,本为果腹,自给自足。盛夏季节,赤日炎炎,逾月滴雨未降,再平常不过,山下平原上种的蔬菜被烈日晒得病怏怏的,又加病虫害高发,虽四海无闲田,颗粒无收仍不可避免。而种在高山上的蔬菜,因有浓雾润泽,兼海拔高,气温低,抑制了病虫害的肆虐,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青菜,无不水灵,光泽亮丽,让人垂涎欲滴,山里人就将高山蔬菜卖到城里,丰富城里人的餐桌。大棚蔬菜兴起后,高山蔬菜因其天然无污染,深受城里人喜爱。
云端小镇的高山蔬菜市场,一大早就车水马龙,一辆辆三轮车,随处可见,买菜的顾客都是商贩,并非居家的主妇,卖菜的指着新釆的蔬菜,自卖自夸,仿佛一季的辛勤,不夸耀一番,便会错失良机。讨价还价,熙熙攘攘,一派产销两旺的样子。收购来的高山蔬菜不仅供天台城里,还销往宁波等地。当人们吹着空调,一边埋头大嚼这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时,想象不出村民在浓雾中耕作的辛苦,湿透衣背的,分不清是雾水还是汗水。

茶禅一味/摄
远看白雾,如梦似幻,如诗似画,让人浮想联翩,即便弄一头雾水,也仿佛是沾了仙气,恨不生生雾里住。但实际上当你住在多雾的地方,那又是另一番天地了。天台北山一带有句民谚:“有囡勿嫁龙皇堂,雾露涽水满眠床。”一天到晚,房里房外床上床下,被褥物什都是湿漉漉的,如何安生!多雾的日子多了,才晒干的被子又被雾水打湿,湿润的被子沉重黏人,将人包裹得更紧,扯都扯不开,说是睡眠,还不如说是整夜用身体烘被子,本地人烘惯了被子,尚能安之若素,初来乍到者,境况窘迫,人地两生,这一夜如何忍受?不得而知,心中萌发的诗意已荡然无存。
有一回,几位朋友下榻在石梁宾馆,相约到大兴坑岭头的农家乐去喝酒,酒桌上推杯换盏,大家喝得兴起,不觉夜深。等宴罢,由没喝酒的我驱车下山,院子里亮着灯,倒车没什么困难,出了院门,我暗叫不好,起雾了,厚重的浓雾犹如毯子一般裹挟了一切,天地混沌不分,车灯只能照出几米远的地方,车上仿佛汪洋中的一叶孤舟,随时都会被波涛掀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不敢再开,下车看了下情况,小心比照道路在雾中的境况,近光灯的亮点与车身的距离,犹豫过是否在山上将就一晚,磨磨蹭蹭好一会,才重新上车,驱动车轮缓缓向前。车到桐天村后的拐弯,浓雾散开,道路复又平坦。我松了口气,这段路不足五公里,此时离宴罢已三十多分钟过去了。

我的老家欢岙,在天台山南麓海拔五六百米处,大雾多发。我十三岁时,家里养了一只牛,用来耕田,农闲时就放养在村后系船山上,系船山是天台山的支脉,峰峦挺秀,牛羊一放上山,非一季半载不下山。春耕临近,父亲让我上山,将家里的牛牵回来。那天雾很大,虽然伸手可见五指,几米之外的来人,就只闻其声了。我约了一个伙伴,就在大雾中往山上走去,山越高,雾越浓厚。路上我们大声说话,彼此壮胆,伙伴也要找牛,没过多久,我们就走散了,我大声呼唤,没有了回音。尽管我戴着箬帽,穿着蓑衣,却早已满脸雾水,额头的雾水不住流入眼眶,用手抹不干净。山雀在枝桠间没命地嘶鸣,给迷蒙而窄小的空间增添了恐怖与不安,尽管这座山是我平常砍柴的地方,再熟悉不过,但在雾中我需要仔细辨认道路与方向。在漫无目的中寻觅,也不知过了多久。突然,转弯处冒出一团黑乎乎的庞然大物,还向我压过来了,我差点被吓瘫,连忙躲到树丛中,定睛一看,原来它就是我家的牛!几个月不见,它长高长大了。
(原《天台山的雾》原作者 王典宇 编辑 朱眉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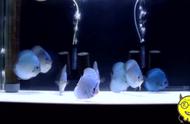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8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8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