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始皇:为什么对秦半两钱的含金量毫不介意?

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益阳市文物处撰写的《湖南益阳兔子山九号井遗址发掘简报》(《文物》,2016年第5期)发表的秦简三二中有这样一个案例:

电影《秦颂》剧照
十月已酉,劾曰女子尊择不取行钱,问辞如劾,鞫审。已未,益阳守起、丞章、史完论刑(字为:左食,右外乃内又)尊市,即弃死市盈十日,令徒徙弃冢间。
十月已酉,查秦代朔闰表,应为秦始皇三十二年(公元前215年)岁首,起诉一位名为“尊”的女子“择不取行钱”,也就是拒收“行钱”,问审及复审均事实无误,当月,由益阳守,按益阳为县,应为名为“起”的县令,县丞“章”,令史“完”定罪为“弃市”,将人杀死后,死尸在“市”暴尸十天,然后让徒隶移“尊”的尸体到乱葬岗丢弃。
也就是说,“择不取行钱”的刑罚是“弃市”死刑,远比《二年律令》中的“罚金四两”为重,而睡虎地秦墓竹简《金布律》也有明确的律文规定:
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,毋敢择行钱、布;择行钱、布者,列伍长弗告,吏循之不谨,皆有罪。
官府受钱者,千钱一畚,以丞、令印印。不盈千者,亦封印之。钱善不善,实杂之……百姓市用钱,美恶杂之,勿敢异。
无论百姓还是官员,还是官府收入,都不允许“择行钱”,而早在《汉高祖刘邦的货币战争》一文中,三解已经写到过:
“半两”是一个重量概念,秦制1两等于24铢,半两也就是12铢,“重如其文”的意思是标准的秦半两钱的重量就应该是12铢。
……在秦始皇陵园西侧的赵背户村,发掘刑徒墓32座,其中29号墓出土半两钱37枚,32号墓出土3枚,直径最大的3.4厘米,最小的只有2.33厘米,最重的6.01克,约合秦制9铢,最轻的1.35克,约合秦制2铢。
在陵园北侧的鱼池村遗址共出土半两钱540枚,多数钱径在2.64-2.83厘米之间,重量在2.20克-3.80克之间,约合秦制3.3-5.7铢。
重量在3-6铢之间的,可以称作中型半两钱,在考古发现中最多,反倒是达到12铢的却并不多。(王冕:《西汉前期货币改革新探分析》)
也就是说,“半两钱”的重量不足“半两”是一个事实,而秦律的律文反复强调也说明,秦朝政府完全知晓这个事实。

电影《荆轲刺秦王》剧照
部分钱币学家指出,“秦半两”的重量随着时代越晚,越接近秦二世时代而越轻,并将其与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中的记载联系:
(秦始皇三十七年)十月,帝之会稽、琅邪,还至沙丘崩。子胡亥立,为二世皇帝。杀蒙恬。道九原入。复行钱。
他们认为,“复行钱”实际上是“改铸小钱”,所以造成了墓葬中“秦半两”的普遍减重。问题是,墓葬中的“秦半两”可以确定下葬时间,却并不能由此确知钱币铸造的时间,两者之间无法等同,所以,并不能以墓葬时间来排列钱币的大小顺序。
而“睡虎地秦墓竹简”《金布律》已经明确地提及“钱善与不善,实杂之”,其墓主埋葬时间为秦始皇三十年,则可知,此前的秦国境内“行钱”已经充斥着“不善”的“减重钱”,所以才要求官府的一视同仁,而上文中涉及到的“择行钱案”,时间已是秦始皇三十二年,在地处边远的“益阳县”也发生了此类案件,都说明秦国、秦朝的货币“滥恶”问题由来已久。
也就是说,秦国、秦朝的“铜币”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或者说能够实现“标准化”来保证“足重”,因为只要在秦律施行的境内,“行钱”的峻法就保证了“秦半两”哪怕经过减重也一样能够通行无阻。
根本原因就在于“秦制”对于“行钱”和“行布”的定位并非是“宝货”,也就是说,并不重视其财富“贮藏功能”,而重点是“行”,也就是专门面向治下编户齐民的财政工具,只要你“用”就“行”了。
这个思维方式,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专门的说道,叫“名目主义”(chartalism),其创始人英尼斯在1913年就提出了,货币是政府债务的“代理人”,货币之所以有价值,是因为政府要求人民用货币纳税。
也就是说,只要“货币”能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“公平”流动,哪怕那是一个“贝壳”,它一样能够拥有“购买力”。
“秦半两”不是“贝壳”,“秦半两”缺少的是“公平”。
根源就在于秦朝的财政体系。

电影《秦颂》剧照
在《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》一文中,三解以“解剖麻雀”的方式回溯了秦代的“地方财政”:
作为“会计部门”,“诸曹令史”手中的“计簿”,才是真正意义的“某县公司账本”,或者说是“资产损益表”,只不过秦代的账本不是用人民币计数的,也不是用半两钱计数的,甚至根本没法“货币化”,所以,也不存在什么“固定资产”和“流动资金”之分,所有账目中的“物”,甚至“人”,都是“流动资金”,并详细分科。
要点就是秦代的“财政体系”根本没有“货币化”,所以只能是以不同科目进行分列,这一点,与上文中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完成“货币化”的会计体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,而这一体系对于“货币信用”的赋予又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,因为它可以保障“货币”以“名目主义”的理解一样,“公平”地流转于“公私之间”。
而秦代的“地方财政体系”中,已知的“货币收入”(不全是“税种”)包括以下几项:
(1)禁钱(县属):“山川所出”,王室垄断的山川池泽出产的手工业原料经“刑徒经济”生产产品售出所得钱,就是“官府作务市受钱”;“园池市井租税之入”,则是“市租、质钱、园池入钱”;
(2)不禁钱(县属):“赎刑钱”和“赀债钱”;
(3)户赋钱(郡属):五月的户赋16钱/户,每年送郡守处,“治库兵车马”。
在此之外的“中央财政科目”缺少资料,但结合西汉《二年律令》推测,或应有“少府”主管的“铸钱”、“采金”为直接的“货币收入”,其余也可以并入上述科目。
而支出项,实际上是两大类:
(1)采购;
(2)功赏。
按照西汉元帝时的政府开支项目,“吏俸”应为“司农钱”的大宗,占总数的50%左右,在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,4号、5号木牍记录了墓主人所在的西乡所辖市阳、当利、郑里等三个里的“算簿”,这些断代为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四年的简牍,“算钱”用途也包含了“吏俸”。
不过,必须指出的是,以上“开支”的基础都是在西汉王朝普遍开征“算钱”之后,这笔收入甚至代替了前述秦朝上缴郡守的“户赋”,而“户赋”则被收归县级收入项目,这是秦无货币“吏俸”的理由之一。

电影《荆轲刺秦王》剧照
理由之二是秦朝地方财政严重依赖“刑徒经济”,在《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》中已有明确的计算:
从秦律规定的徒隶比例来看,2/3的田徒,1/3参与政府服务,则迁陵县的300刑徒应该有200人进入“田官”耕种,以男女1:1为“1户劳力”计算,养活全县的官吏、刑徒的耕地总面积不过5601亩,也就是“1户劳力”耕种56.02亩,完全不超出能力范围,哪怕是编制齐全的“迁陵县”,也就是“1户劳力”耕种80.55亩。
也就是说,“刑徒经济”单独供养整个“公家”绰绰有余,远比通过正常的编户齐民财政获取物资更加“经济实惠”,所以,本质上,“刑徒”的数量是与官僚组织配套的。
这种刑徒规模和地方财政的配套在秦律令中有明确的反映,即人数不足则由“县”向“治虏御史”请求,而“上计”给皇帝的“计簿”也包括“徒隶员簿”,也就是说“徒隶”存在有严格的预算管理,也就是对应“吏俸”的“全谷制”支出。
确认了这一点,再来看“采购”和“功赏”这两个“支出项”,也就是“货币投放”渠道唯此二者。
相对于“采购”的频繁和少量,“功赏”这个科目完全相反,因为“秦制”的赏功虽有“斩首赐爵”的基础,但又有律文明确规定,爵不满一级或达到升爵上限的都要折算成钱,而这单次的赏钱就数以万计。
换句话说,对于普通人而言,“赐爵”远不如“赐钱”常见,而“赐钱”又远不如“政府采购常见”。
所以,仅以秦代的“县级地方财政”来建构“货币收支”模型,实在是微不足道,仅以“上计”所用的“计簿”的科目来看,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钱的科目只有5种,占总量的17.86%。
在此条件下的“货币收支”很难发生难以挽回的后果,对于整个秦帝国财政的影响自然也“应该”微不足道。
问题是,秦朝的“货币回笼”手段非常少,也就是常态的“货币税收”根本不足以赋予“秦半两”足够的“信用”,百姓大部分交的“税、赋”仍是以“实物”和“劳役”的形式进行支付,唯有“户赋”和交易中产生的“市租”、“质钱”是常态的“货币税”,而前者一年不过15钱,后者则是比例抽成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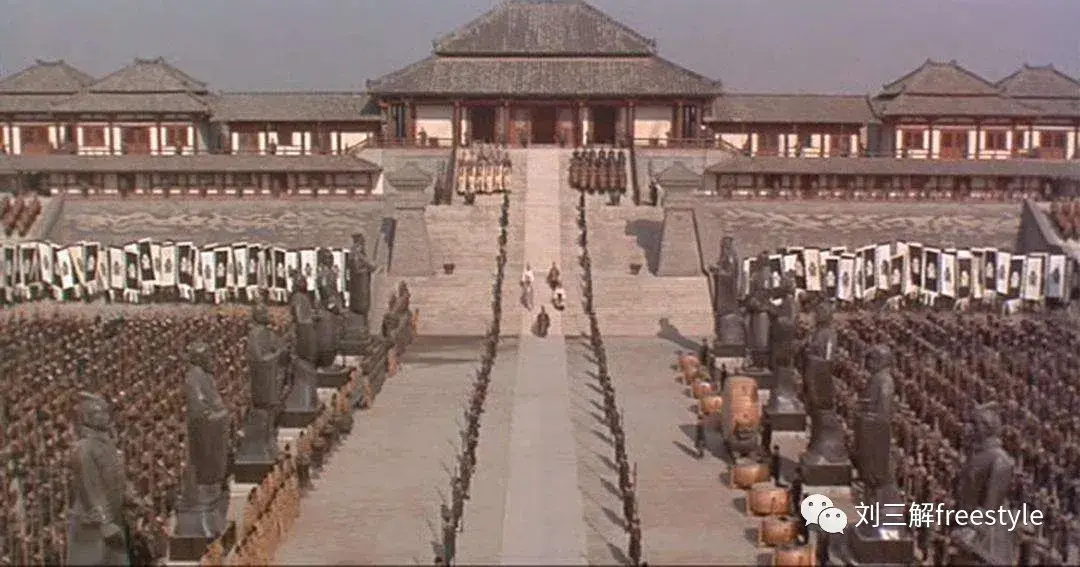
电影《秦颂》剧照
比较之下,“货币投放”的决绝就令人惊叹,见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肆)》:
制诏丞相御史:兵事毕矣,诸当得购赏贳责(债)者,令县皆亟予之。令到县,县各尽以见(现)钱,不禁者,勿令巨辠。令县皆亟予之。丞相御史请:令到县,县各尽以见(现)钱不禁者亟予之,不足,各请其属所执灋,执灋调均;不足,乃请御史,请以禁钱贷之,以所贷多少为偿,久昜(易)期,有钱弗予,过一金,赀二甲。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戊
意思是,在统一战争结束后,秦始皇下诏书,要求各“县”立刻兑现对从军者的“购赏”和“免债”激励,并必须给予“现钱”。但这只是理想的原则,所以丞相、御史大夫请求有所变通,即“县”可以用“禁钱”之外“不禁钱”完成兑现的就尽快下发,如果不够,先各自向“属所执法”申请,由“执法”来负责调剂辖区各县的“现钱”,还不行,就上书御史大夫,请求使用“禁钱”贷给“县”,“县”回头偿还。
简单地说,不够先用“公款”,再调剂,最后再找“皇帝私财”借贷,回头再还。
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“债务关系”:
秦民——县廷——秦王
货币投放时,由秦王私府——“少府”铸造货币,贷给“诸县”,“诸县”再作为“节点”,将货币以上述两种途径,释放给秦民使用。
以“名目主义”的理论来理解,秦民无论是以“受赏”还是“售货”获得的“秦半两”、“行布”,实际上都是一份“一般债务凭证”,也就是将定额的“财富”出借给了“县廷”,而“县廷”则又将定额“财富”出借给了“秦皇帝”。
那么,“秦半两”和“行布”的“一般债务凭证”功能由什么保证呢?
毫无疑问的是,秦朝政府远比英尼斯在20世纪初见识的暹罗国更“精明”,他们采取了一套非常严格的“交易控制”系统来保证“欠缺信用的货币系统”不被“动态”的“市场价格升降”冲垮。

电影《荆轲刺秦王》剧照
“秦制”严格限制境内百姓的自由流动,也就意味着跨区物流和现金流的大规模流动是被禁止的,则“诸县”实际上是一个个独立的“市场”和“货币区”(尽管用的货币是一样的),所以,尽管在“县”内会有非常繁荣和频繁的商品交换,见《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“拜金”社会》,实质上仍是数量的低水平堆积。
而整个秦帝国有数的几个受惠于这种官方垄断物流体系的城市,都是秦帝国的都城,如“咸阳”、“栎阳”、“雍”和“西”,尤其是“咸阳”,作为“太仓”和“大内”的所在地,四方诸县的“剩余物资”都会辐辏聚集,而几大都城、旧都的“官营刑徒经济”才能提供更多样性的“分工”和“商品”,而六国的商人“邦客”也会向其汇集。
这些都是秦国在统一之前,能够长期保持“繁荣”、“强大”的制度条件。
固定“货币区”保证了货币不会自发地向某个区域流动并集中,而物资却可以在行政命令下集中;同时,秦律将“交易行为”严格约束到了“市”内,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,并通过干预和操纵“市”内的商品定价的方式,为货币强制赋予“财富价值”。
正因为如此,上述“择行钱弃市”的律令结合“告奸连坐”的管理手段,可以得到最大效率的执行,也就是说,哪怕“秦半两”被换成了“纸片”,通过对“交易双方”的人身控制,乃至于生命的暴力威胁,“秦制”顺利地赋予了“秦半两”价值。
通俗地比喻一下,就是我自己可以“偶尔”不讲规矩,但我用刀逼着买卖双方守规矩,因为“总算还有规矩”,所以,“信用”产生了,当然,其中多了点“博彩”的成分。

















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8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18号